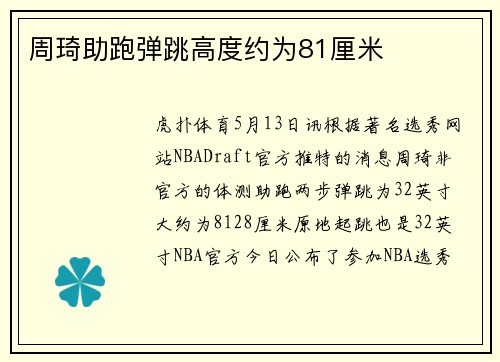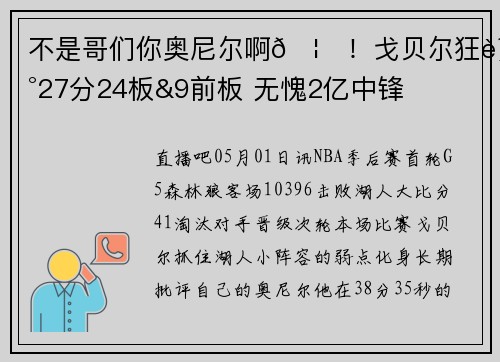
准噶尔汗国与哈萨克汗国的百年战争(1620 - 1757)
- 15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仍有余温。” 17 - 18世纪中亚草原上,准噶尔汗国与哈萨克汗国的百年战争,便是这样一段带着余温的历史。它不仅是两个游牧政权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博弈,更是游牧文明在近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命运写照。这场战争中,宗教传播、火器革命、帝国博弈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最终导致蒙古系游牧帝国走向覆灭,中亚的权力格局也被彻底重塑。接下来,让我们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还原这场波澜壮阔的史诗级冲突。
第一章 战争缘起:草原霸权的真空与争夺
帖木儿帝国崩溃后的权力重组
15世纪,辉煌一时的帖木儿帝国解体,中亚地区随即形成了三大势力:
乌兹别克汗国:牢牢掌控着河中绿洲,以撒马尔罕为核心,尽享这片土地的富庶与繁华。

哈萨克汗国:占据着北部草原,坚守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
卫拉特联盟:盘踞在准噶尔盆地,后来逐渐分化为准噶尔、杜尔伯特等部落。
MK体育恩波利合作伙伴关键转折点:1509年,哈萨克汗哈斯木率领军队,成功击溃乌兹别克昔班尼汗,夺取了锡尔河以北的优质牧场,迫使乌兹别克人南迁。从此,哈萨克成为草原的新主人,但很快便面临着卫拉特诸部的严峻挑战。
资源争夺:生存空间的致命博弈
牧场竞争:17世纪初,准噶尔部人口不断增长,达到约40万,畜群也随之膨胀。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他们迫切需要夺取哈萨克控制的伊犁河谷、七河流域等水草丰美的优质牧场。
贸易垄断:准噶尔为了掌控连接俄罗斯、布哈拉、中国的 “草原丝绸之路”,多次对哈萨克商队进行劫掠。据俄国档案记载,仅在1635年,就有12支哈萨克商队在额尔齐斯河沿岸惨遭劫掠。
战略要地:塔什干作为中亚的商贸中心,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商人和货物,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巴尔喀什湖拥有丰富的淡水与盐资源,是维持游牧生活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这两个地方成为了双方必争之地。
宗教与意识形态对立
准噶尔的藏传佛教扩张:噶尔丹早年前往拉萨潜心学经,被五世达赖授予 “博硕克图汗” 称号。此后,他试图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逐步渗透至哈萨克草原。
哈萨克的伊斯兰化:15世纪,哈萨克接受了伊斯兰教,此后,哈萨克贵族常常以 “圣战” 的名义动员牧民。18世纪的《阿布赉汗法典》更是明确规定了对异教徒战争的战利品分配规则。
第二章 战争进程:三个阶段的血火交织
第一阶段:拉锯与试探(1620 - 1688)
关键事件:
1620年冲突:准噶尔首领哈喇忽剌率领军队进攻哈萨克中玉兹,无情地焚毁了突厥斯坦城郊的牧场,就此拉开了百年战争的序幕。
1635年雅梅什湖之战:哈萨克头克汗联合吉尔吉斯人奋起反击,成功歼灭准噶尔3000骑兵。然而,这并未能阻止准噶尔继续西进的步伐。
1680年准噶尔转型:噶尔丹引入瑞典军事顾问雷纳德,在乌尔扎尔建立兵工厂。此后,该兵工厂每年可生产火绳枪2000支、火炮50门,大大增强了准噶尔的军事力量。
战略态势:准噶尔凭借先进的火器优势,逐步蚕食哈萨克东部的牧场。而哈萨克则利用游击战术,不断袭扰准噶尔的补给线,双方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
第二阶段:准噶尔霸权巅峰(1689 - 1739)
准噶尔的全面攻势:
1698年塔什干战役:策妄阿拉布坦率领2.5万精锐部队,一举攻陷塔什干,处决了哈萨克苏丹头克汗之子,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大玉兹不得不臣服。
1723年“大灾难”:准噶尔采用残酷的 “焦土战术”,焚烧了哈萨克的春牧场,导致30万牲畜死亡,中玉兹人口锐减四成,给哈萨克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1730年萨雷苏河之战:哈萨克名将博拉特率领敢死队,趁着夜色突袭准噶尔大营,成功缴获18门火炮,暂时扭转了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哈萨克的分裂:1731年,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向沙俄宣誓效忠;中玉兹阿布赉汗向清朝朝贡;大玉兹则沦为准噶尔的附庸,哈萨克汗国陷入了分裂的困境。
第三阶段:清朝介入与准噶尔覆灭(1740 - 1757)
决定性转折:
1745年准噶尔内乱:噶尔丹策零去世后,诸子为争夺汗位展开激烈争斗,这场内乱引发了瘟疫与饥荒,准噶尔人口从60万急剧骤降至20万。
1755年清军西征:乾隆帝采纳 “以夷制夷” 的策略,联合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共同夹击准噶尔。兆惠率军一举攻占伊犁,成功俘获达瓦齐。
1757年阿睦尔撒纳叛乱:哈萨克阿布赉汗积极配合清军围剿叛军,最终在额尔齐斯河畔将准噶尔残部全部歼灭。
战后格局:哈萨克名义上臣属于清朝,但沙俄通过《奥伦堡条约》(1734)、《中玉兹归附书》(1740)等手段,逐步控制了哈萨克的领土。
第三章 军事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对抗
准噶尔的军事近代化
火器革命:
准噶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工体系:
塔尔巴哈台铁矿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保障了生产的基础。
乌苏冶炼厂日产生铁2000斤,强大的生产能力为军工制造提供了坚实支撑。
伊犁兵工厂能够仿制奥斯曼式臼炮,其射程可达800米,大大提升了准噶尔的火力。
据传教士南怀仁记录,1696年昭莫多之战中,准军火炮齐射的威力巨大,曾使清军 “人马俱碎”。
军事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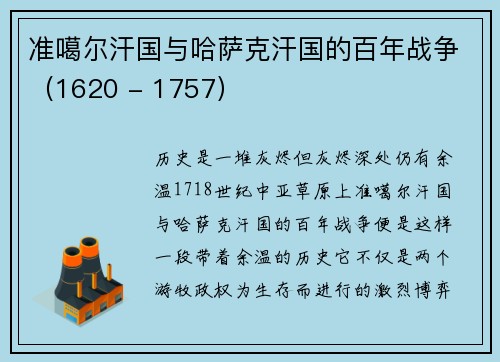
“乌卢斯” 制度:将属民编为40个 “鄂托克”,这是一种集军事与行政为一体的单位,每鄂托克需提供750名骑兵。
特种部队:
包沁 (炮兵营),凭借强大的火力成为战场上的攻坚力量。
巴图鲁 (重甲突击队),身着厚重铠甲,冲锋陷阵,锐不可当。
和硕特哨骑 (轻装侦察兵),行动敏捷,负责侦察敌情。
哈萨克的社会困境
玉兹制度的缺陷:
三大玉兹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调,甚至还会为了争夺利益而互相攻伐。1725年,中玉兹巴拉克汗曾与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为争夺锡尔河牧场爆发内战,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实力。
经济基础脆弱:
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使得哈萨克难以支撑长期的战争。1733年准噶尔封锁期间,哈萨克的物资匮乏,用100匹马才能换取1支火绳枪。
战术代差:
哈萨克仍以传统骑射为主,军事战术相对落后。直到1750年代,才组建了首支火枪队,但仅500人装备土耳其火绳枪,在战场上难以与准噶尔抗衡。
第四章 大国博弈:清朝与沙俄的暗战
清朝的“双轨战略”
军事打击:康熙三次亲征(1690 - 1697),雍正设立军机处统筹西北战事,乾隆朝更是投入白银6000万两用于西征,展现了清朝对准噶尔问题的高度重视。
政治分化:1739年册封阿布赉汗为 “哈萨克总管”,默许其向沙俄称臣,巧妙地制造了哈萨克双重臣属的状态,以此来分化和制衡各方势力。
沙俄的渗透策略
要塞链条:沿额尔齐斯河修建奥伦堡(1735)、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1752)等要塞,形成了一道坚固的 “哥萨克防线”,逐步向中亚地区渗透。
经济控制:通过俄哈贸易垄断皮毛收购,1750年哈萨克对俄出口占其总贸易额的73%,从经济上牢牢控制了哈萨克。
文化同化:在阿克莫林斯克(今阿斯塔纳)设立俄语学校,培养亲俄贵族子弟,试图从文化层面同化哈萨克。
第五章 战争遗产:重塑中亚文明版图
人口与生态剧变
准噶尔灭绝:清朝实行 “尽行剿灭” 政策,准噶尔人口从鼎盛期120万(含附属部族)急剧降至1759年的不足5万,曾经强大的准噶尔汗国几乎消失殆尽。
草原荒漠化:持续不断的战争对牧场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斋桑泊周边曾经 “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美景不复存在,变成了 “黄沙白草无人烟” 的荒凉景象。
文化记忆的重构
哈萨克史诗:《阿布赉汗的四十勇士》将战争神圣化,塑造了 “抗准英雄” 的集体记忆,成为哈萨克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帝国的叙事:《平定准噶尔方略》将战争定性为 “讨逆统一”,为现代中国西北疆域奠定了法理基础。
地缘格局的定型
沙俄的胜利:通过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沙俄完全吞并了哈萨克草原,成为这场百年战争的最大赢家。
清朝的局限:尽管设立了伊犁将军府,但清朝未能深入中亚腹地,这为19世纪西北边疆危机埋下了隐患。
结语:游牧文明的近代化困境
这场百年战争充分证明,传统游牧社会在面对集权化政权与火器革命时,其松散的联盟体制与单一的游牧经济暴露出了致命弱点。准噶尔的覆灭标志着延续两千年的游牧帝国模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哈萨克的 “双重臣属” 则预示了近代中亚沦为大国博弈场的悲惨命运。当沙俄哥萨克的火枪与清朝的红衣大炮在草原上轰然作响时,一个属于马背民族的辉煌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